油灯昏黄如豆,在土坯墙上投下摇曳的影。
白锦书猛然睁眼,额间冷汗浸透鬓角,指尖无意识地抠进粗布被子里,鼻间萦绕着经久不散的草木灰气息。
喉间像是塞了团浸水的棉絮,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半分声响。
脑海中翻涌的记忆碎片几乎要将她撕裂——学堂里先生讲授《诗经》的声音、绣着并蒂莲的蜀锦鞋、还有母亲鬓边那支总沾着夜露的玉簪,俱都与眼前漏雨的房梁、散着霉味的陶罐、以及床头那盏豁口油灯格格不入。
“锦书醒了?”
木门“吱呀”一声推开,穿青布衫的妇人端着粗陶碗进来,鬓角沾着麦秸,碗里飘着两三片泛黄的菜叶。
白锦书望着她佝偻的脊背,喉间突然滚过原主的记忆,这是养了她十八年的“娘”,可此刻看来,那抹身影竟比隔雾的山影还要模糊。
“娘……”开口时声音带着久病的沙哑,白锦书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颈间,触到一片温润的冰凉。
她怔住了,那是块羊脂玉佩,雕工古朴的螭龙纹在灯光下泛着微光,尾端系着半旧的绛红丝绦。
原主的记忆里,这是她从小戴在颈间的物什,养母总说“是你亲娘留下的”,可除此之外再无半句。
妇人将碗搁在斑驳的木桌上,汤水晃出几滴,在桌面积成浅洼:“醒了便喝些菜粥,病了这几日,可把人折腾坏了。”
她伸手欲摸白锦书额头,指尖却在触到玉佩时猛地一抖,像是被火烫了般缩回。
这细微的动作没逃过白锦书的眼睛。
她垂眸望着碗中浮油,突然记起昏迷前的情形——原主在河边浣衣时摔了一跤,醒来便成了她。
可此刻在脑海中翻涌的,却不是原主的记忆。
而是另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她本是深宅大院里的千金,晨起要向母亲问安,午后要习女红,晚间父亲会教她读些《列女传》……首到某个暴雨夜,她跟着乳母去花园捡风筝,再醒来便在这陌生的农家。
“玉佩……”她指尖捏住螭龙尾端,抬眼望向妇人,“娘可曾说过,这玉佩上的纹路是何意?”
妇人正用袖口擦桌的手顿住,目光在玉佩上逡巡片刻。
突然转身掀开土灶上的铁锅,蒸汽裹着野菜的涩味涌出来:“妇道人家懂什么纹路,你自小戴着的物件,问这些作甚?”
她说话时背对着白锦书,声音却比平日高了几分,铁锅与木勺相撞发出刺耳的声响。
白锦书盯着她绷紧的肩膀,心中泛起涟漪。
原主的记忆里,养母从未如此回避过这个问题。
她低头望着玉佩,螭龙纹雕刻得极为精细,龙首微昂,爪握玉珠,正是官宦人家常见的“苍龙教子”纹。
这样的玉佩,怎会出现在农家女身上?
夜色渐深,窗外传来父亲晚归的脚步声。
白锦书借着如厕的由头,摸黑绕到柴房后。
月光从云隙间漏下,照着她颤抖的指尖——左腕内侧,三粒朱砂般的小点排成斜线。
这是原主从未留意过的胎记,却与记忆中母亲常说的“眉间朱砂痣,腕上三星连”暗合。
“他爹,那丫头今日问起玉佩……”养父母的卧房传来低低的交谈,白锦书贴着土墙屏住呼吸。
养父的嗓音带着常年劳作的沙哑:“当年在官道旁捡她时,襁褓里就裹着这玉佩。
你忘了那伙山贼?
若让她知道亲生父母是……”话尾突然被截断,接着是瓷碗搁在桌上的脆响。
山贼?
官道?
白锦书咬住唇,指甲几乎掐进掌心。
原主的记忆里,养父母从未提过她的身世,只说“是从后山捡来的”,如今却扯出山贼与官道,其中必有隐情。
她望着手中玉佩,螭龙的眼睛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像是藏着无数秘密。
回到卧房,白锦书吹灭油灯,却毫无睡意。
她细细梳理着脑海中的两段记忆:原主的人生充满了劳作与贫寒,而另一段记忆里的生活却精致优渥,两者唯一的交集,便是这块玉佩。
她记得在“另一段人生”里,母亲曾说过“待你及笄之年,便将传家玉佩给你”,可眼前的玉佩,分明比记忆中的还要陈旧几分。
更蹊跷的是,当她想起“另一段人生”的父母时,心底竟涌起真切的思念,仿佛那些温声细语、那些疼爱目光,本就是属于她的。
而反观养父母,虽有十八年的养育之恩,此刻却像隔着一层薄纱,连他们的面容都显得模糊。
鸡啼三遍时,白锦书终于摸到枕边的玉佩。
螭龙的纹路在掌心凹凸分明,她突然想起父亲书房里的典籍——《古玉图谱》中记载,“苍龙教子”纹始于前朝,非贵胄之家不得佩戴。
她一个农家女,怎会有这样的玉佩?
晨光初绽时,养母端着菜粥进来,见她盯着玉佩出神,欲言又止。
白锦书突然抬头,目光灼灼:“娘,我左腕的三颗痣,可是生来便有?”
妇人手中的碗晃了晃,菜汤泼在袖口:“你这孩子,怎的尽问些古怪话?”
她转身去拿抹布,声音却低了下来,“许是生来便有的,娘也记不大清了……”记不大清?
白锦书望着她慌乱的背影,心中的疑虑更盛。
若真是亲生父母,又怎会记不得孩子的胎记?
她低头看着腕上的三点红痣,突然想起昨日在河边浣衣时,邻村的王婆子曾说:“锦书这模样,倒不像是山里长大的,倒像那大户人家的小姐。”
大户人家的小姐……白锦书咬住唇。
她容貌清秀,皮肤虽因劳作有些黝黑,却难掩细腻,手指修长,掌心虽有薄茧,却不似常年握锄的农女那般粗糙。
这些细节,从前被原主忽略,此刻却像被串起的珍珠,在她脑海中连成一条线——她极可能是被拐卖的贵女,而养父母,或许知晓些内情。
“爹昨日说,我是从后山捡来的?”
白锦书突然开口,目光紧紧锁住养母的背影,“可后山距官道甚远,爹怎会在官道旁捡到我?”
妇人的动作猛地顿住,手中的抹布“啪嗒”掉在地上。
她转身时面色苍白,嘴唇动了动,却被推门进来的养父打断:“大清早的,吵什么?”
他肩上扛着锄头,鞋底沾着新泥,目光在白锦书脸上扫过,很快移开。
白锦书望着他不自然的神色,心中己然明了。
她不再追问,低头喝着菜粥,却尝不出半点滋味。
养父母的回避、玉佩的来历、胎记的巧合,种种线索都在指向一个可能——她本是官宦人家的女儿,幼时被拐,流落到这山村。
晨光透过糊着桑皮纸的窗棂,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白锦书摸着颈间的玉佩,突然想起“另一段人生”里,父亲曾说过的话:“无论何时,都要记住自己的根。”
如今,她的根究竟在哪里?
是眼前这漏雨的土坯房,还是记忆中那座雕梁画栋的侯府?
这一日,白锦书如往常般去河边浣衣,却格外留意起过往行人。
她发现自己对官话极为熟悉,听到商队谈论京城轶事时,竟能听懂那些文绉绉的言辞,而原主本应只懂方言。
更蹊跷的是,她能认出商队马车上的纹饰——那是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的云雷纹。
暮色西合时,白锦书坐在门槛上,望着天边最后一丝霞光。
养父母在灶间低语,声音混着柴火的噼啪声传来。
她摸了摸腕上的红痣,又抚过玉佩上的螭龙纹,终于下定了决心——无论前路如何,她都要查清自己的身世,哪怕这意味着要离开生活了十八年的农家。
是夜,白锦书将玉佩贴身藏好,望着窗外的明月。
她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但她清楚,从摸到这块玉佩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便不再是那个日复一日浣衣耕作的农家女。
或许前方有荆棘,有阴谋,但她无所畏惧,因为她是白锦书,是那个在记忆中被疼爱、被呵护的千金,更是此刻清醒而坚韧的女子。
油灯终于熄灭,土坯房陷入寂静。
白锦书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听着养父母均匀的鼾声,心中却翻涌着巨浪。
她不知道,就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一座朱漆大门的侯府里,一对夫妇正对着半幅残破的画卷垂泪,画卷上,一个三岁女童抱着玉佩笑得灿烂,腕间三颗红痣如落英般娇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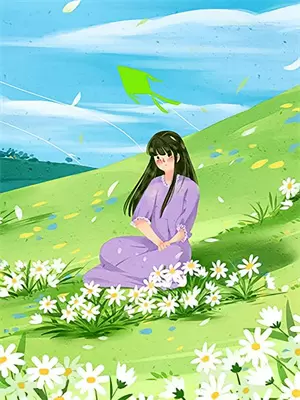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