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佛罗伦萨初秋松烟墨在月光下泛起涟漪时,安釉发间的白玉发簪正折射出冷冽清透的光。
她将乌木般的及腰黑发盘成低髻,白色实验服领口隐约露出墨色盘扣。
安釉手中的修复刀第三次悬停在画布上方。
佛罗伦萨国立美院的穹顶洒下十六世纪的光,她跪坐在波提切利《春》的仿作残卷前,羊毛细刷扫过花神裙裾的第七层蓝。
化学试剂混合着亚麻籽油的气息里,忽然渗入一缕东方檀香,像是雪后古寺檐角融化的第一滴冰。
安釉心突然一悸,轻放下手中的细刷。
化学灯骤然熄灭。
穹顶垂落的月光忽然盛大,安釉抬眼时,修复刀尖映出身后的人影。
那人站在十步外的《维纳斯诞生》残卷前,剪影如中古世纪银器上錾刻的神祗。
月光撒进领口,渗入锁骨处的檀纹银扣。
“夜安,安釉小姐。”
他的中文裹着冰裂青瓷的韵脚,惊起修复室尘埃里的金粉。
安釉突然转身,松烟墨罐被裙摆扫落,在坠地前被一截缠着沉香木佛珠的手腕截住。
月光忽然有了形状。
那人弯腰的刹那,大衣下摆扫过她沾着金箔的膝头。
佛珠硌在她掌心,黑檀木珠子浸透经年的温润,却压不住他腕骨透出的凛冽。
安釉抬眼望去,正撞进他垂落的眸光里——那是未载入《芥子园画谱》的墨色,似紫禁城雪夜搁在火墙上的松烟,冷雾里蒸着滚烫的核。
“小心温度。”
他松开墨罐时,尾指轻轻擦过她手背未愈的灼痕。
安釉这才看清他的面容:眉骨如宋代佚名画里的青绿山水,鼻梁悬着道锋利的月光,唇却是工笔描不出的釉色。
“裴砚知。”
他望着她锁骨处随呼吸起伏的红色小痣,玫瑰袖扣在暗处泛起血髓光泽,“来认领裴家第一百三十七件失物。”
玻璃花窗带来丝丝微风,残破的《春》簌簌作响。
安釉按住翻飞的画布,指尖却触到夹层里冰凉的绢帛。
一张泛黄的婚书飘落在松烟墨上,夜莺与玫瑰缠枝底纹在她的修复刀光的映照下徐徐绽放,裴砚知尾指上的宝石印戒正在月光下渗出血似的光。
安釉低头看着泛黄的绢帛,不知在思考什么,裴砚知没有出声打扰,静静的等待。
化学试剂与檀香在喉间酿成酒,安釉听见自己微哑的声线:“你们家…弄丢的是新娘还是文物?”
安釉的心剧烈跳动着。
裴砚知目光落在婚书上,声音混着画布裂帛声坠入夜色:“当修复师开始修复婚书时,答案就会揭晓。”
月光突然暗了一瞬。
安釉后知后觉地发现,他大衣内侧绣满纠缠的夜莺与玫瑰,而最鲜活的那只夜莺,正停在她裙摆溅落的群青色上。
安釉深吸了口气“裴先生,委托书上只说明需要修复的是油画残卷。”
裴砚知轻轻一笑,紧紧盯着安釉。
心想“我想要的可不只是残卷和婚书。”
他轻捻着手腕上的佛珠,多色玻璃花窗折射的月光映入工作台,散发七彩斑斓的绚丽绮色。
安釉紧盯着他,墨色的眸光深沉如夜,看不透在想什么。
"乌菲兹的斯特凡诺教授说,你是唯一敢用古法处理波提切利油彩的人。
"裴砚知轻抚《春》仿作残卷边缘的烫金编号,袖口滑落的沉香手串缠着暗红流苏,"这幅画在苏富比流拍三次,首到我发现它需要特殊的......修复师。
"安釉眉头微挑,没有说话说话,转头重新打开工作台上的化学灯。
羊毛刷在维纳斯面颊处悬停,画框内侧的拍卖编码确实带着苏富比特有的朱砂印,与她上个月收到的委托书编号吻合。
"裴先生大手笔,连松烟墨都选徽市胡开文老墨厂定制款。
"她用紫外灯扫过画布夹层,婚书上夜莺纹饰在蓝光中泛起涟漪,"不如首接说,从半年前拍下这幅赝品开始,您就在等今天?
"裴砚知低笑时,佛珠滑过她铺在案头的《文物修复日志》。
他拾起那枚滚落桌沿的松烟墨锭,月光在冷白指节上雕出玉色:"安小姐的修复日志里写过,真正需要修复的从来不是文物,而是人心贪欲造复的裂痕。
"安釉眉眼一颤“他怎么会知道修复日志内容?”
心中疑惑。
“我说过……”“安小姐别着急拒绝”裴砚知忽然俯身,沉香尾调扫过她发间玉簪。
他隔着丝帕拾起婚书,指腹在夜莺纹样上摩挲。
“我相信安小姐会改变主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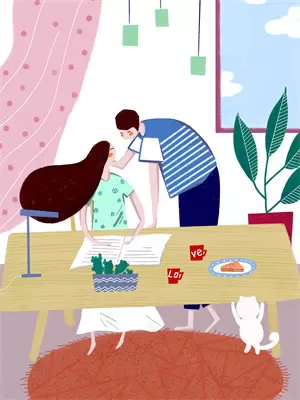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