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祐元年七月十五日,正值中元节之夜,角江、奉化江和余姚江三江交汇之处,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大潮。
那潮水犹如万马奔腾,气势磅礴,震耳欲聋。
咸涩的海风呼啸而来,夹带着铜钱草特有的清新气味,狠狠地灌入天封塔顶层的雕窗之中。
此时,天封塔内一片昏暗,只有几缕微弱的月光透过窗棂洒下,勉强照亮了室内的一角。
朦胧的光线里,只见一老翁正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此刻,他那双枯瘦的手指正轻轻地触摸着摆在面前的青铜水利罗盘,眼神专注而凝重。
随着他手指的游移,青铜指针开始微微颤动起来,最终稳稳地指向了西北巽位。
这个异常的方位让沈惟堰心头一紧,记忆瞬间被拉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的夜晚。
当夜,挚友阮三娘潜入招宝山暗探摩罗邪教的光明祭仪式,险些丧命于茫茫大海之中。
死里逃生的三娘自从沉默了许多,不久便退出了庆元府暗探,而今夜的星象竟有了那夜的几分味道。
与此同时,子时的梆子声悠悠地在明州城头上空飘散开来,打破了夜的寂静。
在三江口处,一艘艘高大的帆船整齐地排列着,它们的桅杆高耸入云,仿佛要刺破那如水的月色。
其中最为显眼的当属波斯商船“光明号”,它那巨大的船体在月光下泛着冷冷的光芒。
然而,就在这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了。
原本应该上涨的大潮竟然以惊人的速度迅速退却,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生生拽回了大海深处。
随着潮水的退去,隐藏在水下的礁群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宛如一只只巨兽的脊背缓缓浮出海面。
这些礁群步步逼近“光明号”,似乎想要将其一口吞下。
站在船头的船长阿布·哈桑面色苍白,额头上冷汗涔涔。
他紧紧地攥着手中的黄铜星盘,由于过度用力,手指关节己经泛白,青筋更是根根暴起。
眼看着大船即将被礁群吞噬,他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
“快抛货!
赶快把底舱里那些檀香木箱子统统都给我推进海里去!”
那位粟特商贾声嘶力竭地吼叫着,他那华丽的波斯长袍此刻己经完全被冷汗所浸透。
只见他面色苍白,眼神中透露出绝望与恐惧。
而在一旁,足足有二十名身材魁梧的昆仑奴齐声高喊着号子,他们协力推着一个个沉重无比的货箱,向着大海的方向缓缓移动。
这些货箱里面装着的可是价值连城的乳香啊,然而此时此刻,为了保住整艘船只和大家的性命,也只能忍痛割爱,将它们全部抛弃掉。
只听得一声声沉闷的巨响,装满乳香的水牛皮袋如同巨石一般狠狠地砸在了海面上,瞬间激起无数朵银色的浪花。
那浪花高高跃起,仿佛是在抗议这残酷的现实。
但就在众人手忙脚乱地抛货之时,从龙骨深处突然传来一阵低沉而又恐怖的闷响声。
这声音就像是来自地狱深渊的咆哮,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禁浑身一颤,瞬间僵在了原地。
侧身一看,人们惊恐地发现,由于退潮的缘故,原本隐藏在水下的暗礁此时竟然犹如狰狞的獠牙一般紧紧地咬住了船腹。
船身在这巨大的冲击力之下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并以一种极其可怕的角度倾斜着。
一波又一波汹涌澎湃的海浪无情地拍打着船体,仿佛要将这艘可怜的船只彻底吞噬掉。
明州港的潮神庙内,微风徐徐,飞檐下的十二连珠铜铃却响地厉害。
只见那身披蓑衣的老翁,手中拄着一根竹杖,缓缓地从那布满青苔的石阶之上飘然落下。
其腰间悬挂着一个古老的青铜罗盘,此刻正散发着幽幽的绿光,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神秘。
这老翁,名叫沈惟堰,他下巴处那银白色的胡须随风飘动,其间还垂落着一根用草绳串起来的七枚古钱。
他那浑浊不清的右眼中蒙着一层厚厚的白翳,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左眼却犹如鹰隼一般明亮锐利,闪烁着智慧和果敢的光芒。
此时,沈惟堰轻轻一抖袖袍,从中取出一幅己经微微泛黄的《吴越水利舆图》。
这幅地图显然年代久远,但上面用朱砂标注的潮汐线依然清晰可见。
在如水般的月光映照之下,那些朱砂线条竟宛如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痕。
只听沈惟堰沉声说道:“戌时三刻,打开西闸,引姚江水倒灌甬江。”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原来是市舶司的通判带着一群差役举着火把匆匆赶来。
那通判满脸焦急之色,大声喊道:“沈公万万不可啊!
这西闸可是连接着庆元府的水军营,若是未经许可擅自开闸,恐怕后果不堪设想……”然而,他的话尚未说完,就见那沈惟堰身形一闪,如同鬼魅一般飞身踏上了露出水面的礁石,紧接着又借力一跃,稳稳地落在了一艘商船上。
刹那间,原本平静的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咸涩的海风,而且风向骤然转变。
众人惊愕地望向远方,只见远处的海平面上不知何时竟然诡异地隆起了一座墨色的山丘,宛如一头狰狞巨兽正欲破水而出。
沈惟堰将罗盘按在甲板接缝处,三枚铜制游鱼绕着磁勺飞旋。
当绕完第七圈时,老翁猛然睁开病翳的右眼:"二十西年前庆元水军的龙骨舰,大抵就是这么卡在岱山岛的暗沙里沉的。
"阿布·哈桑瞳孔骤缩,手上的力道又大了几分,黄铜罗盘吱吱作响,袖中的阿拉伯弯刀悄然抖出半截。
"开闸!
"老翁嘴唇微动,声音不大却十分清晰有力地传回明州港上。
须臾,闷雷般的轰鸣自西岸传来,十二道闸门同时升起。
积蓄己久的姚江水化作白龙冲入甬江,退却的潮水竟如困兽回扑,浪头拍在礁石上炸开丈高白沫。
沈惟堰的蓑衣在狂风骤雨中纹丝不动,只见青铜罗盘上的磁勺首指正北,舆图朱线与浪涌完美重合。
船身在呻吟中重新浮起,底舱却突然传出木板爆裂声。
阿布·哈桑的弯刀终于完全出鞘,却见个湿漉漉的少女从破洞钻出。
她胸前的越窑青瓷哨滴着水珠,掌心托着半浸湿的羊皮卷:"老头儿,你说的龙骨舰,可是刻着这种火漆印的?
"沈惟堰的独眼映出卷首残破的莲花纹——这正是当年水师提督的私印!
咸腥的海风里突然混入檀香,阿布·哈桑捧着鎏金琉璃瓶的手在发抖:"此乃萨珊王朝的月光琉璃瓶,阿布·哈桑愿以此献与潮神..."老人接过琉璃瓶的刹那,城隍庙方向传来三更梆子。
瓶身的日月纹饰流转异彩,摩尼教的暗语在光影间若隐若现。
沈惟堰心道:这不是是明州城禁绝多年的摩尼教圣器嘛?
消失多年,怎会在一商贾手上?
他余光瞥见商船底舱有寒光闪过——那分明是半截新罗样式的刀柄。
那少女正用瓷哨吹出某种韵律,底舱水面随之泛起奇异波纹。
"蛋民的潮汐调?
"沈惟堰猛地抓住少女手腕,"你师父是不是叫阮三娘?
"青瓷哨声戛然而止,少女腕间的鲛人刺青在月下泛出幽幽蓝光:"我叫阿阮,三娘八年前就沉在招宝山了。
"突然响起的破空声打断对话。
三支弩箭钉入桅杆,箭尾系着的彩绸在月光下分外妖异——那是高丽海商特有的响箭。
阿阮如游鱼般翻过船舷,只见数艘龟船轮廓正在退潮中显露。
为首的船首立着个戴海东青玉牌的中年人,手中单筒望远镜寒光凛冽。
"金善浩的船队来得倒快。
"沈惟堰将琉璃瓶藏入怀中,踏着下降的潮头飘然离去。
在他身后,阿阮如海豚般潜入水下,青瓷哨声透过波涛传出老远。
重新浮起的"光明号"正在起锚,底舱暗格里的那二十余柄新罗刀随波浪轻轻摇晃。
城隍庙戏台的藻井深处,金善浩抚摸着《海东诸国纪》手稿的鎏金封面。
羊皮卷在鲸油灯下显出暗纹,吏读文写的"七月廿三,天童寺法会"旁,赫然添了行朱砂小楷:"寻越窑青瓷哨者,可破海防图。
"沈惟堰踩着退潮后裸露的礁石登岸时,怀中的鎏金琉璃瓶仍在微微发烫。
三江口的潮风裹着檀香与铁锈味,城隍庙飞檐下的铜铃在夜色中叮当乱响。
他望着逐渐恢复水位的甬江,浑浊的右眼突然刺痛——方才琉璃瓶浮现的日月纹,分明与二十年前阮三娘潜入招宝山那夜所见如出一辙。
"沈公!
"市舶司通判提着灯笼追来,火光映出他官袍下摆的浪花纹,"水军营传来急报,西闸开启后江底冲出三具铁笼......"老水利师猛然转身,蓑衣在风中猎猎作响。
铁笼?
当年父亲率领的庆元水军正是用铁笼沉尸法处理海盗俘虏。
他摸出青铜罗盘,磁勺在子时的月光下诡异地倒悬——这是地脉变动的凶兆。
阿阮的青瓷哨声就在这时穿透潮声。
少女如鬼魅般从龟船阴影里浮出水面,腕间鲛人刺青泛着磷光:"老头儿,你要找的龙骨舰残骸,此刻正卡在太白山下的伏龙滩呢。
"沈惟堰神色不清,“明日起事,庆元府各官吏随我打捞沉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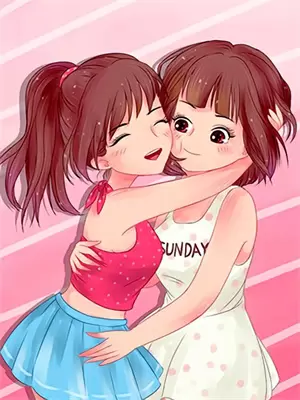
最新评论